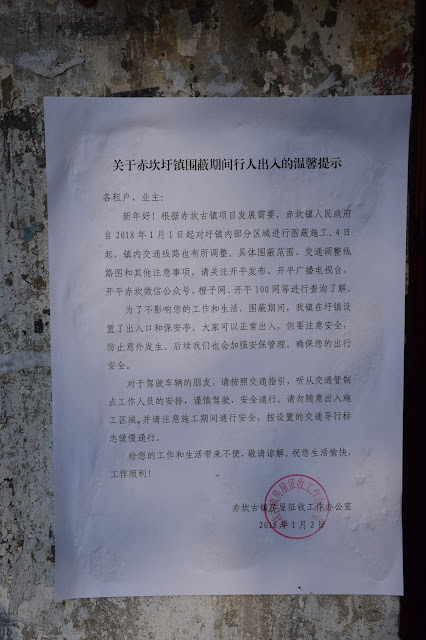後來才發現,關於善良、體貼、認真、細心,都是一次次無關輸贏的溫柔競爭、沒有詞性變化的比較級:Kind, Kind, Kind。
和同事P飛過幾次,因為批數相近又同年,少了年齡和資深資淺的隔閡,共事時好自在。雖然在工作之外彼此並沒有交集,但一直覺得她是位善良溫吞的女孩,偶爾飛到,甚是安心。
那次和她一起飛東南亞,飛時四個半小時,流程包含發送綜合果仁和飲料的考克服務(cocktail)。我和P同廚房、不同組工作,我和我的夥伴負責左邊走道、P和她的夥伴負責右邊。如同前幾次的飛行經驗,P動作總是優雅、不疾不徐。當我們這邊的餐已經發完,P那邊還有四、五排客人沒拿到餐;在走道上收垃圾時,也往往是左側收完一輪,再繞到右邊幫忙。我承認一開始自己對P的「優雅」有些不以為然,或許是自己剛上線時曾因動作緩慢被責難,後來不論是倉促的短班、或是漫漫長夜越洋班,服務時我都以迅速、效率為最高宗旨,而這樣日積月累的「自我督促」下,手一碰到餐車、一拿到餐盤,腎上腺素就會以火山爆發的氣勢伴我咻完一次又一次的工作。
當完成飲料服務,大家紛紛拿著盤子在客艙收拾垃圾。我會把乘客塞在杯裡的包裝袋拿出來集中在盤子前方,將空杯子五個一落整齊堆疊,若杯子裡還有些剩餘的液體,就把髒衛生紙塞進杯子裡吸水獨立放置,我對自己的機靈與效率自豪。
當我一如往常捧著一盤殘羹回廚房時,遇見了正將一杯杯液體往水槽倒的P。身旁的另一位同事訕笑的說「這是誰點的特調嗎?」,原來P細心的把每個杯裡殘餘的飲料都集中在一起,先把杯裡的液體都清乾淨,才把乾杯子丟進垃圾桶裡。
第一次看到有人這麼做,我沒多想的取笑起她,「你也太麻煩了吧,才一點點水而已,垃圾桶裡那麼多衛生紙和廢紙,遲早會把它吸乾的阿。」
P張著她黑得澄澈的眼睛看著我,聲調有些提高的問,「難道你就算杯子裡有水,也都直接往垃圾桶丟嗎?」
第一次被溫柔和藹的P如此質問,我有些嚇到,「就......如果不是一整杯都沒喝的話,只剩一點就會直接丟掉......」
P垂下眼搖了搖頭,不再多說。此刻的我感到臉頰泛紅發窘,為了自尊心又說了幾句,但越是辯駁,越顯得自己的粗糙。
後來,P和我說,有次地停時她坐在廚房邊,看到負責換垃圾袋的大叔把垃圾袋從桶子裡拿出來,對著空的垃圾桶大嘆了一口氣,他好奇的看過去,傾斜的垃圾桶裡積了一角顏色混濁的液體。從那次之後,為了不再造成清潔哥姐的困擾,她要求自己讓垃圾桶滴水不沾。
那一刻,我才知道P和我是多麼不同。一直以來我所追求的體貼,都專注在與我互利共生的同事、客人身上,看似體貼,說穿了更像以自我中心為出發點的錦上添花;而P在大部分人眼中的慢郎中和多此一舉,或許才是跳脫自我藩籬、綜觀全局的大器。回想起我每次洋洋得意生成的算計,原來我的心只容納得下一架飛機。
感激公司上千個同事、每天翻新的排列組合,讓我能遇見如P般善良的靈魂,再在每一次的相形見絀後,學習怎麼活得像個人。
 |
| 小動物也有善良之分嗎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