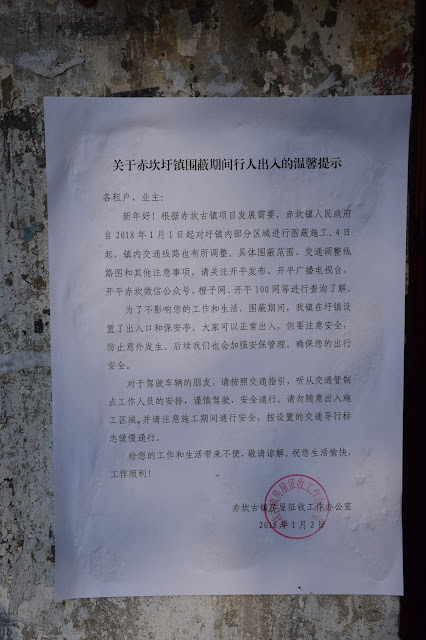宿舍一樓掛著大大的交流白板,是住宿生寫下生活碎念的地方。有呼籲大家在樓梯間講電話時小點聲,或是尋找一件在曬衣場丟失的裙子。而我總會在白板角落偷偷畫下一隻貓,儘管常常被認作小豬。
晚上經過白板,看到一段留言,留言者希望大家在浴室洗手台漱口時,身子能往前彎一些,讓吐出的漱口水不會噴到身旁的人。平常對白板上那些「上完廁所記得沖水」、「在廚房煮完菜垃圾要帶走啊」這類生活訓斥已見怪不怪,看到這則留言卻格外激動,「這不是我入住第一天晚上就在心底吶喊的事嗎!」,是種他鄉遇故知的動容。
和舊識聊天時,總會在語句裡輕描淡寫對某些事物的想念。我用在太安靜的廁所如廁時,那股控制括約肌縮放的節制,依序釋放眷戀,輕輕的、少少的,就怕自己聽見。我想念那條朝氣道早問好的走廊、想念為了展現親切而上揚的嘴角和頷首、想念每個當下我認為是小題大作、事後回想卻又有幾分道理的貼心(首次感到這樣的後知後覺,是在330看到4L幫離開座位的G2按住椅子讓椅子不會彈回去,等G2回來可以方便一屁股坐下的時候)。
被擠壓在高空中小小廚房的人們啊,或被逼迫或自願,把身上的稜角摩得溫順光滑些,為了讓彼此在這狹小的空間活得舒適一點點,頭挨著腳、腳挨著身。
第一次體悟廚房外世界之粗糙的(不是貶義,純粹相對),是九月初入宿那天,借出一條手機充電器,給忘記從家裡帶來的小妹妹室友。宿舍離台北車站商圈步行十分鐘,想說她隔天去旁邊買一條線後,充電器就會回來了。怎知時間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過去,期間我甚至開始責怪自己的記性,是不是小妹妹根本已經原物交還,是我不長記性忘記(後來趁他不在、小偷似的站在他書桌前研究,才確認充電器還安好的收在他的櫃子邊)。直到中秋連假結束的早上,我看到充電器終於擺回我書桌中央,白色的線俏皮的兜圈。翻箱倒櫃回想,啊,我十八歲時也如是嗎?
記得剛和R在一起時,常常因為他的舉止沒有符合飛機上的細膩標準而皺眉,偶弄得不歡而散。例如坐計程車時給司機模稜兩可的指示、走在路上撞到旁人卻不自覺,或是點菜時耽誤服務生太久。現在回想起來,當時我應該也正努力和細膩磨合著吧,便不自覺的把別人眼中笨拙的自己,反射到無辜的R身上了。說不上來為什麼,現在和R相處時,那股煩躁再也沒出現。這是得道,還是被細膩束縛住了呢?
願做一個以細膩耕耘書海的農夫,被草割了不喊痛、陽光曬得不怕流淚,直到雙手長滿厚實溫暖的繭。
晚上經過白板,看到一段留言,留言者希望大家在浴室洗手台漱口時,身子能往前彎一些,讓吐出的漱口水不會噴到身旁的人。平常對白板上那些「上完廁所記得沖水」、「在廚房煮完菜垃圾要帶走啊」這類生活訓斥已見怪不怪,看到這則留言卻格外激動,「這不是我入住第一天晚上就在心底吶喊的事嗎!」,是種他鄉遇故知的動容。
和舊識聊天時,總會在語句裡輕描淡寫對某些事物的想念。我用在太安靜的廁所如廁時,那股控制括約肌縮放的節制,依序釋放眷戀,輕輕的、少少的,就怕自己聽見。我想念那條朝氣道早問好的走廊、想念為了展現親切而上揚的嘴角和頷首、想念每個當下我認為是小題大作、事後回想卻又有幾分道理的貼心(首次感到這樣的後知後覺,是在330看到4L幫離開座位的G2按住椅子讓椅子不會彈回去,等G2回來可以方便一屁股坐下的時候)。
被擠壓在高空中小小廚房的人們啊,或被逼迫或自願,把身上的稜角摩得溫順光滑些,為了讓彼此在這狹小的空間活得舒適一點點,頭挨著腳、腳挨著身。
第一次體悟廚房外世界之粗糙的(不是貶義,純粹相對),是九月初入宿那天,借出一條手機充電器,給忘記從家裡帶來的小妹妹室友。宿舍離台北車站商圈步行十分鐘,想說她隔天去旁邊買一條線後,充電器就會回來了。怎知時間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過去,期間我甚至開始責怪自己的記性,是不是小妹妹根本已經原物交還,是我不長記性忘記(後來趁他不在、小偷似的站在他書桌前研究,才確認充電器還安好的收在他的櫃子邊)。直到中秋連假結束的早上,我看到充電器終於擺回我書桌中央,白色的線俏皮的兜圈。翻箱倒櫃回想,啊,我十八歲時也如是嗎?
記得剛和R在一起時,常常因為他的舉止沒有符合飛機上的細膩標準而皺眉,偶弄得不歡而散。例如坐計程車時給司機模稜兩可的指示、走在路上撞到旁人卻不自覺,或是點菜時耽誤服務生太久。現在回想起來,當時我應該也正努力和細膩磨合著吧,便不自覺的把別人眼中笨拙的自己,反射到無辜的R身上了。說不上來為什麼,現在和R相處時,那股煩躁再也沒出現。這是得道,還是被細膩束縛住了呢?
願做一個以細膩耕耘書海的農夫,被草割了不喊痛、陽光曬得不怕流淚,直到雙手長滿厚實溫暖的繭。
 |
| 期中考結束的週末,第一次爬象山。 |